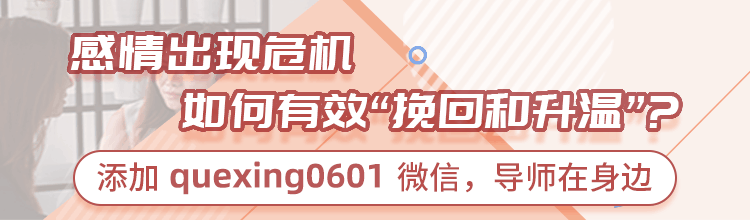内心想离婚却不舍孩子怎么办 我想用孩子毁掉他的二婚美梦
2022-05-14 10:14:12 梦悠网
与小强离婚时,我三十六岁,女儿多多刚满五岁。小强在餐桌上提出离婚。内心想离婚却不舍孩子怎么办,那是多多的生日,我做了一桌菜。
当他说离婚两个字的时候,刚夹了一只鸡腿放进碗里,淡淡的语气就像是在评价鸡腿的味道。
 我惊呆了,不相信地抬头看着他。
我惊呆了,不相信地抬头看着他。
小强说:我写了协议,车,房子,孩子都属于你。至于存款,我们还是一人半。毕竟,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了。
他的话说得流畅,改变了过去结巴的习惯。
平静的语气里没有半分对这个家的不舍和愧疚。
看起来,已经练习了很多次。
我把一一块姜片放进嘴里,呛口的辣味便通到胃里,有隐隐的痛。
小强接着说:我喜欢别人,三年前的事。别怪我,我真的不能留在这个家里。
他厚颜无耻的坦诚让我束手无策,我竟然有些反应。
小强后来也说了一些我不太记得的话,脑海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我们站在被推翻的残羹冷炙上大打出手。
生活终于把我们变成了彼此最恨的人。
一旦脸被撕破,就没有必要坚持下去。
我让小强改变协议,我要车,房子和票子,只是不要孩子。
家散了,我的世界崩塌了,我还留下孩子做什么?
那一刻,我承认我疯了,我失去了所有的理智。
小强似乎没想到我连女儿都不想要,站在一旁不停地说我残忍。
我冷笑,半斤对八两,谁也不比谁高贵。
他想离开我们去迎接新的生活,我又怎能让他如愿?
孩子,是我留给他的唯一障碍。
我们都知道,但是没有人说出口。
有些话,留在心里才是最伤人的。
我们陷入了僵局,小强的脸很不好看。他一再妥协,甚至答应给我所有的积蓄。
我笑了,你以为法院会把孩子判给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母亲吗?
在小强的骂骂咧咧中,我们终于完成了手续。
走出民政局,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在路的尽头分手。
十年的婚姻,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生命的变数,总是让人措手不及。
正午的太阳很热,耀眼的光线刺痛了我的眼泪。
小强打电话说多多要找我。
对着屏幕,我冷笑着让他死。
在家里睡了很多天。
那天早上,妈妈带着多多给我送饭。
当我打开门的时候,多多一眼就看到了我,她紧紧地抱着我,喊着妈妈。
毛茸茸的小脑袋贴在我的大腿上,柔软的身体散发着孩子独特的香味。
她的头发乱蓬蓬的,裤腿上溅满了泥,整个人看上去很脏。
她眯着眼对我微笑,咧着嘴微微翘起,很像那个刚刚抛弃我的男人。
我伸出的手在半空中突然收回,转身向客厅走去。
你是怎么把她带回来的?我趁着多多去厨房给我拿碗的那一刻问妈妈。
小强送来的,他说孩子想你
他说要我你送来?难道你不知道孩子是被判给他的吗?我强忍着怒火抱怨。
妈妈,你不要生气,是我让奶奶送我回来的,你为什么不和爸爸住在一起?多多仰着小脸站在我身后,拉着我的衣角。
问你爸去!我把她捏在手里的衣角拉出来,以后,别来找我。
多多被我的反应吓到了,她睁大眼睛看着我。
在灯光的照射下,晶莹的泪珠在独特的蓝晶莹的泪珠。
我妈伸手去抱她,她转过头,拱起妈妈的怀里:奶奶,妈妈为什么要生气?我不好吗?那我能保证以后再也不生病吗?
多多搂着奶奶的脖子,脸却拼命转向我。
奶奶拍了拍孩子的背,安慰她:不,妈妈今天只是心情不好,跟多多没关系。奶奶会带你去超市吗?
好吧。孩子清脆地回答,然后从奶奶身上滑了下来。她跑进储藏室,从超市市的购物袋,牵着奶奶的手,向门口走去。中途,她突然把它折回来,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递给我。
上次她住院的时候我买了那块巧克力,放久了,巧克力表面已经变得有点软了。
她把它塞进我的手心,对我微笑,然后像头鹿一样飞快地跑开了。
房间里立刻安静下来。站在二十楼的阳台上,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,有一种莫名的悲伤。
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连婚姻都经营不好,为什么那个男人要这么狠心地辜负我?
握手,有眩晕的感觉。
不知过了多久,依稀听到门响,接着是妈妈和多多的哭声。
妈妈拖着我的手,多多抱着我的脚。
老人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手背,有点不舒服。
我听到她在耳边说:女儿啊,你是不是抑郁症?为了一个臭男人,千万想不开啊!
他们扶着我躺在沙发上,多多赶紧跑进卧室,拿着毯子。
毯子太重了,她几次差点摔倒。
她躺在沙发上挣扎着把毯子盖住我,赶紧站起来拿袋子里的糖果。
软的,硬的,橘子味的,草莓味的,红的,绿的,铺满了整个沙发。
多多用小手轻轻地拉着我,她说这些都是为我挑的,问我喜不喜欢。
我懒得说话,转身让她走开。
母亲说我状态不好,离婚不是多少错,我不应该把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她。
我知道妈妈说的是对的,但是我不能接受离婚的事实。
只有把问题归结到多多身上,我的心才能找到暂时的平衡。
母亲说,这样对多多不公平。
但是谁又对我公平了?
我对坐在我旁边的妈妈狂吼,完全无视还在客厅里的多多。
多多是个残疾人,出生时就患上了一种叫瓦登伯格综合征的疾病。
这种病天生蓝眼,所以也叫蓝眼宝宝。
名字很可爱,但是病情却让人无法喜欢,通常表现为听力受损。
这种病不常见,发病率约为四万分之一。
不幸的是,多多就是这四万分之一。
由于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,所以了解的人并不多。
起初,我们都以许多特别的眼睛为荣。
那个冬天,我带让大家看到她神秘的蓝眼睛,我带着她参加各种场合,同事的升迁,朋友的婚宴。
我承认,我是虚荣的。每当人们赞美我的美丽时,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。
我沉浸在做母亲的喜悦中,没有闻到危险的气息。
多多出生时,我和小强的经济都不是很好。
请保姆也是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村阿姨,所以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多多的病情。
为了给多多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,刚出月子我就回到公司工作。
起初小强不同意,他觉得我应该多和孩子们呆在一起。
但是,生活的压力,孩子的开销,让我毅然回到了公司。
产后新生儿复查当天,由于公司暂时需要我手头的数据,所以在做最后一次听力检查时,我提前把多多交给保姆回家。
后来,听保姆说,多多看到我离开后一直哭。
因此,医生没有对她进行更详细的检查。
那时,我忙升职,忙着赚钱,没有意识到听力筛查对多多的重要性。
正因为如此,我们直到多多快五个月才发现她的不同。
她听不到声音。她听不到除夕的鞭炮;她听不到我在她耳边摇的拨浪鼓;我对她吼叫,她听不见;我在她面前痛哭,但她还是听不见...
之后,我们带着二人去了所有的医院。
医生说没有遇到太多这样的病例,建议我们去大医院复查。
最后,在省儿科医院,医生诊断出病情。
得到结果的那一刻,我的天塌了,当初我炫耀的时候有多骄傲,现在有多沮丧。
多多的病有点严重,医生说她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。
从医院回来后,小强搬到了书房,他不愿和我说话。
那段时间,家里的气压很低。
后来,为了照顾多多,也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,我很快就辞职了。
我以为这样的牺牲可以换来小强的理解,可是我错了,我在他心里已经被判了死刑。
用小强的话来说,我伤害了很多。
小强又开始抽烟了,我劝他戒烟,他用右手拿着香烟指着多多说,不抽烟还不能生优生儿。
事实上,多多病属于基因病。
医生说,治疗后她戴上人工耳蜗,基本生活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
检查回来后,我们给多多戴上了助听器。
但是孩子太小了,耳朵里突然多了东西显得很不习惯。
因此,哭闹成了家常便饭。
小强太吵了,冷着脸把多多的助听器摘下来。
这样的次数多了,多多就更不愿意穿了。
辞职后,我打算把多多送到康复中心进行培训,但小强拒绝。
康复中心在他眼里是骗钱的。
我现成的大活人不用,那就是脑病。
不过,我并不专业,多多跟我说话也不好。
考虑到助听器效果不佳,多多三岁的时候,我去省城帮她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。
由于费用比较高,我用信用卡分期付款。
为了避免吵架,我没有让小强拿钱。
之后,我陪着二人组开始接受听觉和语言康复训练,不管有多辛苦,我都希望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。
不过,我和小强的感情从此凉了下来,内心想离婚却不舍孩子怎么办,再也没有温度了。